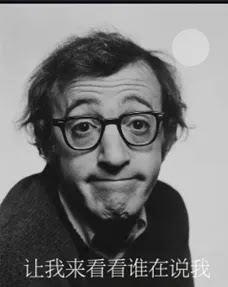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
微语录精选 1231:普通人的解药是钱
@管埋员:有钱人的解药是爱,普通人的解药是钱。
@菊厂刘掌柜:牛肉价格 5 年新低,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意见差异很大,互不理解。
比如养牛的角度看,我老表养牛 10 来年了,现在一头牛卖出已经亏 1600 元了,母牛都要卖掉为了降低损失,他今年至少亏了大几十万。老表强烈的说,不要进口那么多低价牛肉,保护养殖者。
站在消费者角度看,牛肉现在二三十元一斤,以前太贵了,现在价格稍微便宜了点,为什么牛肉比猪肉贵那么多,应该越便宜越好。
按照经济学规律,市场经济由消费者决定并获利,便宜的产品会更受欢迎,大概率老表的生意,不太会好起来。
@青春的泥沼:我之前就说过啊,中国人太实在了,中国这些搞金融的总有一种观念:有借有还。我一直说你看看人家美国,那样多国债怎样还,我反正想不出来。大家要学习美国的国债,慢慢接受一种理念 —— 借了钱为什么要还?
@李建秋的世界: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市值 74 亿美元。
川普搞了一辈子房地产,这个也赢那个也赢,
从市政府弄个项目喜得美滋滋,
没想到这刚进入金融圈,干了一辈子房地产还没有自己媒体上市值钱
和金融比起来,房地产那都算实业
@九边 Pro:性格即命运,主要也是在每次做选择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懦弱的,勇敢的,激进的,脑子有病的,最后可能所有选择都带着性格的烙印。
@t0mbkeeper:傲慢、贪婪、淫欲、嫉妒、暴食、愤怒、懒惰,七宗罪,就是七个流量密码。
@t0mbkeeper:2024 年 12 月 28 日,假马斯克账号发了一条,问谁能说出一件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有人回答火药、造纸之类,然后这个账号就强调说 “本世纪呢?” 显然,他并不是真的想问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当然,他在 2024 年 12 月 28 日发出这个内容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真正有趣的是一个韩国的号对该问题的回答:
“虽然有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发明的记载,但这些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古代韩国曾位于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但随着中国势力的南下,他们编造了极为扭曲的历史。即使在现在,如果发现了文物,也往往选择重新掩埋而非进行发掘,因为一旦发掘出来,就会发现几乎全是古代韩国的文物。”
The Roots of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Attacks in China/中国“报复社会”袭击的根源
Repressive Rule Is Creating a Climate of Isolation and Grievance
Peidong Sun
A tribute at the site of a deadly car attack, Zhuhai, China, November 2024 Tingshu Wang / Reuters
A series of violent attacks across China in recent months have pierced a tightly controlled society’s veneer of stability. In late September, a 37-year-old man killed three people and injured 15 others in a stabbing spree at a Shanghai supermarket. In October, a 50-year-old man injured five people in a knife attack in Beijing. Then, on November 11, a 62-year-old man drove into a crowd in the southern city of Zhuhai and killed 35 people and injured 43 others in what is thought to be one of China’s deadliest acts of criminal violence in decades. In the days that followed, a mass stabbing by a 21-year-old student killed eight and injured 17 at a vocational school in Wuxi, near Shanghai, and a car attack left several schoolchildren and parents injured outside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orthern Hunan Province.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20 such attacks in China this year, with a death toll of more than 90 people.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called these incidents “isolated” and offered explanations emphasizing individual motivations: the driver in the Zhuhai car attack was unhappy with his divorce settlement, for instance; the Wuxi attacker had failed his exams. But taken together, the attacks reveal deep and widespread ruptures in Chinese society fueled by economic stagnation, systemic inequality, and social immobility and exclusion. As a result, such incidents have come to be known as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attacks.
A comparative stud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reat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2022 found that China accounted for 45 percent of the mass stabbings reported across the globe between 2004 and 2017. Its share can be attributed not only to the widespread availability of knives and strict gun control but also to sociopolitical tensions, including severe financial stress. Violent acts in China often target random victims in public spaces and are sometimes performative; in other words, the point is not to accomplish a specific goal but to draw societal attention. Although the state’s extensive censorship apparatus effectively stifles extended public discourse on mass attacks, the California-based nonprofit China Digital Times has documented surges in online activity after such incidents—indicating intense public interest—before posts are erased by censo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ict controls have only exacerbated the problem. Violence underpins China’s social order, and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attack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part as a response to structural violence perpetrated by the state itself, including the silencing of dissent, and other strategies for control such as the one-child policy. Public attacks are often reactions to repression; the irony is that the government generally responds to them with even more repression. After the attack in Zhuhai, for instance, local authorities swiftly imposed a reporting ban, forbade mourning in public, and sanitized the site. And the state mobilized its legal and surveillance capacities in a top-down enforcement of short-term stability, a hallmark of the CCP’s crisis management.
Such responses come at the expense of steps that would address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inciting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attacks. If the CPP clings to a 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tyle of governance, societal fractures are bound to intensify. Without systemic reforms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China risks fostering a cycle of frustration and unrest that could increasingly erupt into violence and even threaten the country’s long-term stability.
DEEP ROOT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struggled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an increasingly educated populace. There are projected to be more than 12 million new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2025, a vast oversupply considering the country’s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of 18.8 percent. (In reality, the rate is likely higher because the data excludes active students.) A dearth of meaningfu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as created limits on upward mobility. Grueling workloads and diminishing opportunities for advancement have taken a psychological toll on workers, especially younger ones. In response, many young people have embraced quiet defiance, including through the “lying flat” movement, which emerged in early 2020 and involves eschewing advanced careers (and even favoring blue-collar or gig work), adopting minimalist lifestyles, and renouncing traditional aspirations such as marriage or home or car ownership to protest social pressures that spur relentless competition and conformity. For others, the defiance has become louder. The researchers Ma Ziqi and Zhao Yunting have hypothesized that “social exclusion,” which can include feeling systemically barred from financial advancement or ostracized because of a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s a driver of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attacks because such exclusion fosters isolation, resentment, and despair.
Economic stagnation only fans the flames. In China, increases in both GDP growth and wages are slowing, and the cost of housing and education are rising. These developments are driving financial insecurity among Chinese people, diminishing their hopes for a stable and prosperous future within the current system. The economic squeeze has also helped exacerbate inequality. The richest one percent in China now controls more than 3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wealth, whereas the bottom half of the population controls only six percent—a stark picture of resource polarization in a putatively communist country that values egalitarian outcomes and what the CCP calls “common prosperity.”
The legacy of state violence is also critical. China’s one-child policy, enforced from 1980 to 2016, disrupted family dynamics and relied on coercive, intrusive methods, including forced sterilizations and abortions. Although the policy achieved the goal of slowing population growth,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hreats to China’s economy today is the profound demographic imbalance that resulted: a vast number of aging retirees reliant on the state or their children for support, and too few people of prime working age. The state largely disregarded the longer-term human costs of the policy, including sustained inequality, deepened mis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estabilization of societal cohesion and political order. Indeed, even after the government lifted the one-child policy, the birthrate continued its rapid decline, falling by half between 2016 (18.83 million births) and 2023 (9.02 million). This was due in part to the policy’s lasting socioeconomic effects: among other things, it both normalized small families and instilled a belief that having many—or any—children could derail a couple’s finances and careers.
One of the policy’s most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is the plight of shidu (bereavement) parents, who have suffered the premature death of the only child allotted to them under the old system and cannot conceive another. Every year, more than 76,000 parents join this group, which faces particularly acute forms of marginaliz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ldren offer both emotional fulfillment and economic security for aging parents; they also confer social value, the absence of which can lead to ostracism. These problems are compounded by inadequate state support; aging parents who have lost an only child are eligible for a one-time state payment of around $4,600, a fraction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most parents would expect to receive from their offspring. Shidu parents embody the broader consequences of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which by prioritizing control over welfare, fosters a systemic neglect that heightens social grievances and may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the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phenomenon. A recent Chinese film documentary chronicled how the desperation of one shidu couple even pushed them to the brink of carrying out a public attack.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have fueled a variety of demonstrations in recent years: shidu parents, for instance, protest annually in front of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Beijing to demand that the state keep its promises of care and support; in 2022, people organized mass boycotts of mortgage payments to protest a housing crisis and “white paper”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strict measures imposed under China’s “zero COVID” policy. These outcries highlight growing discontent across diverse groups and, for many, represent a protest against decades of repression. For much of the Chinese public, the current state violence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more totalitarian repression suffered under Mao Zedong from the early 1950s through the decadelong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ended with Mao’s death in 1976. People had no recourse during the brutal violence of that era, given the state’s total control of the country’s resources and narrative. Those days are long gone, but the legacy of that violence lives on.
FOOL ME ONCE
Together, these forces have resulted in an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es with little chance for release. And unaddressed grievances have helped create a climate in which people embrace violence out of desperation. The CCP’s oppressive governance only compounds the crisis. Responding to violent attacks or mass expressions of discontent, the party, in a thirst for control, has historically relied on a few main strategies that are only likely to intensify. Among the most central are enhanced surveillance and policing. China’s already extensive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advanced facial recognition, social-credit scoring, AI-driven monitoring—is expanding further.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Crowd Emotion Detection and Early Warning Device system, which officials claim can analyze the behavior and emotions of large groups of people, could be used to help detect unrest, underlining the state’s efforts not only to respond to attacks but to preempt them altogether. Additional measures, such as an increased police presence near schools and in public spaces and heightened monitoring dur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periods, evoke the security models in regions such as Xinjiang,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for years systemically repressed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 minorities in what has become a de facto provincial police state.
As the sociologist Xueguang Zhou has noted, the CCP’s approach relies not just on mobilization but also propaganda, which dovetails with the party’s censorship and narrative management. The swift deletion of critical commentary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ublic discourse ensure that mass attacks are framed as isolated incidents rather than symptoms of deeper systemic failures. By controlling the narrative, the CCP seeks to prevent public outrage and copycat incidents while maintaining its image of authority. But these heavy-handed measures, in turn, perpetuate feelings of alienation and agitation among China’s people, increasing the risk of more attacks.
Wu Si, the former editor in chief of the history journal Yanhuang Chunqiu, has said that “hidden rules” govern Chinese society—informal systems that are “neither ethical nor entirely legal” yet sustain the social structure. But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attacks suggests that the party’s indifference to certain rights and its squelching of dissent may be having an unintended effect: the rise of violence that may appear apolitical on its face but constitutes a desperate rejection of the political status quo. And if the party fails to exp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reduce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and injustices, it may eventually find itself faced with greater challenges than revenge against society attacks.
记得前一阵子BB机炸真主党的事么?
好歹有中文字幕的了:记得前一阵子BB机炸真主党的事么?这不,拨云见日很久了,电视台采访了操作该事件的以色列特工,就是他们筹划了此案。他们的设计、启动过程及结果和影响都在这15分钟里。犹太人花十年布一网,做的天衣无缝,任谁也逃脱不了。而且这些BB机经过了很多测试,比如确保只有机主会受伤,而且只让他受伤而故意不让他死,这都是有原因的……看完这段真是五味杂陈。
吹捧六代机,等于猪仔吹捧屠夫手里的屠刀
文/ELM
【1】
这两天墙内最热闹的新闻莫过于中共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的“国之重器”纷纷亮相:
爱国粉红五毛战螂们好比被打了一针又一针鸡血,激动无比,都自觉地开始扬眉吐气,东升西降,东风压倒西风。更有甚者,把六代机上天和毛泽东冥诞联系起来,说自从1840年以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军用重武器装备如此扬眉吐气,一天之内,空军的两款六代战机同时昂首冲天,海军那艘震撼世界的四川舰也宣布下海,而且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诞辰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的感召下,再次站起来了。
随便搜搜,论坛里的鸡血帖是真的不少,单单看标题,排山倒海的爱国气势都要透出屏幕了:
甚至连版面上如果不谈六代机,都会有爱国战螂跑过来表示奇怪:
【2】
是啊,中共军队出了六代机,为什么不说呢?是怕了吗?
——这个问题是真的尴尬,不是自己感到尴尬,而是为五毛战螂们感到尴尬。除了这种鸡血,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表达你们的爱国热情的?想了半天,没有了啊!
直接上个图先:
爱国五毛战螂很生气,说你怎么总是说什么吃得放不放心、喝得安不安心、工作累不累、生活苦不苦、家里穷不穷、养老管不管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怎么不关心跟自己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国之重器”这样的大事!?是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像中国的任何“大杀器”好事都与他们无关,对他们都没有任何好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爱国五毛战螂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不是说鞭子没抽到自己身上,鞭子就不存在了。
然后呢?战螂就很机灵地把话题转到了六代机的技术真伪上,很机灵地绕开了这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如果落后就要挨打,那么现在有了六代机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那应该就不会挨打了吧?
【3】
抱歉,虽然有了六代机,但好像没什么变化,中国人还是被挨打的状态:
随便搜搜,在六代机上天两天之后,12月28日,莫桑比克发生骚乱,首都马普托暴力频发,不少华人商店遭洗劫一空:
华人商店被洗劫一空,六代机在哪儿呢?海军的舰艇在哪儿呢?战螂和粉红在哪儿呢?哦,都忙着嘴炮庆祝是吗?
这些抢劫商店的强盗有没有说一句:哇这是中国护照,太厉害了我们好怕怕,我们不抢了,有吗?或者:中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别抢了吧?或者:来一句粉红战螂最喜欢听的话:哎呀中国都有六代机了,我们怕死了,我们别抢华人了吧!
——哦豁,啥都没有,六代机有了,不落后了,但还是被抢,甚至中国墙内的媒体上都基本看不到自己的同胞被抢劫的新闻。现在你发现六代机的作用了吧?不是给你们这些P民撑腰的,而是来给新闻404的。
华人不仅仅要挨老外的打,更多的时候是挨中国人自己的打。
比如这两天还不停歇的“巴西比亚迪奴隶工人”事件:堂堂的天朝上国,外派的工人不说比当地工人享受更好的条件吧,竟然连经济落后的当地政府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中国这是把工人当成奴隶啊:
这个时候,六代机派上用场了吗?能派上用场吗?会派上用场吗?会不会到了地方,却亮出机身上刷的闪亮的BYD(比亚迪)标志?不是去解救工人的,而是去跟当地的比亚迪撑腰的?
更不要说2024年发生在中国的此起彼伏的献忠事件,这已经不是挨打了,而是赤裸裸的社会残害事件:11月19日,湖南省常德市39岁男子在小学生排队入校时驾车冲撞人群;11月16日,江苏省无锡21岁男子持刀造成8死17伤;10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50岁男子持刀砍伤两名成年人和三名小学生;10月8日,广州市天河60岁男子持刀刺伤三人;9月3日,山东泰安东平县佛山中学附近,一校车冲上校门外人行道致11死13伤;5月20日,江西省贵溪市文坊镇一45岁女性持刀闯入明德小学,致两死10伤;……
六代机起飞了,这些社会献忠事件就能绝迹了吗?这都是中国人害中国人的案例,举不胜举,请问六代机和大军舰能保护普通老百姓吗?老百姓挨打挨杀,跟是不是落后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有关系,那么现在中国科技这么发达,五代机六代机都上天了,为什么老百姓越来越没安全感?如果没关系,那么五毛战螂们这些鸡血激动又在干什么?
——哦,真理部让你们激动,你们就激动。很好,你们认识到了自己奴才的身份。
既然是奴才,就要搞清楚,你们在主子眼里,也只不过是炮灰和韭菜,只不过是养猪场里一头头肥猪,卖力地吹捧屠夫手里的屠刀对你们来说没啥好处。屠刀越锋利,只是屠宰肥猪的时候越趁手罢了,只是社会主义铁拳砸下来的时候更有力罢了。
回到前面图片的那几句话:作为炮灰和韭菜,有了六代机和大军舰之后,你们的工作稳定吗?你们的养老问题考虑了吗?你们的软肋孩子安全吗?你们的消费降级了吗?你们的房贷还清了吗?你们的医保还有钱吗?你担心一不留神就被献忠吗?你出国更方便了吗?……
这些问题,都不是六代机能解决的,也不是大军舰能解决的。
或者说:恰恰相反:因为屠宰场需要钱去搞六代机和大军舰,所以你们的生活越来越难。
【4】
萧伯纳说: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列宁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爱国五毛战螂们不读书,不过这两句话总归看得懂吧?
五毛是带任务出现的,就不说了;普通中国人在吹捧六代机之前,还是要搞清楚:你可以自豪,但要搞清楚,你到底在自豪什么。你吹捧的东西,能带给你起码的平等、安全和尊严吗?
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
微语录精选 1230:二级市场没有对与错
@劳阿毛: 出差与客户吃晚饭,席间问我是否喜欢车模,我有点吃惊没敢说话,临别时,客户拎来个精美的盒子,说送个车模摆件留作纪念,不成敬意…
@何夕: 二级市场没有对与错,只有赚与赔。禁止从业者炒股,真的非常遗憾…… 这让他们可以心安理得的胡说八道,不知道自己有多菜。
@Samuel 叔: 疫情放开后这两年,一脸尿泡农相张口每年赚几千万的人越来越多,一背调兜里还是三瓜两枣
@南郭刘勃: 把辟邪剑法和独孤九剑(假设两种武功炼成了水平都差不多)大量印刷分发到武林群豪手中 。任何人只要愿意自宫就可以练辟邪剑法,只有个别人拥有练独孤九剑的天分,很快,练独孤九剑的人就会成为武林公敌。
@Tianfxd:你的 [直觉、违和感,有 90% 都是正确的
总觉得哪里不舒服莫名搞不懂这个人点定说不上来但感觉不对劲
当你对一个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千万不要和这个人扯上关系。
定不要舍不得放不下,不要过度怀念沉没成本,因为你们相处的越久,你越会发现一个惊碎你三观的真理,那就是,这个人大概率比你预料的还要糟糕的多。
不要忽视潜意识发来的求救信号,那个才是高维的你,对你最大的保护
@Seif_:我童年看的是不可播放,青春期读的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该页无法显示,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一些您访问的页面已被删除。哈哈,哈哈哈哈
@idben : 收到一个冷冻包裹,里面有两只鸡,是家里养的宠物鸡。
「因为有感情了,所以不敢吃。想说你都没有住家里应该没有感情,所以寄给你吃。」
@神嘛事儿: 我发现不管你干什么工作,后缀加上「仙人」两个字,气氛就会变得很抽象,比如
会计 —-> 会计仙人
程序员 —-> 代码仙人
公务员 —-> 公务仙人
UP 主 —->UP 仙人
快递员 —-> 快递仙人
最扯的是这个:总裁仙人
@在也门钓鲑鱼:豆瓣灵异组其实很科学。有人发帖问,今天和朋友见面,发现他脸上淡淡发着绿光是什么原因。
回帖:面膜里有荧光剂,快让他别用了。
让年轻人崩溃躺平的社会,将比年轻人更快崩溃
文/锐知一刻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直接来看50多年前的一项实验。
1972年6月22日,时任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脑进化与行为实验室主任的学者约翰·邦帕斯·卡尔霍恩(John Bumpass Calhoun)站在伦敦皇家医学会的讲台上,在这座拥有200多年历史的皇家医学会中,向听众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一项长期实验,名叫“老鼠乌托邦”(Mice Utopia Experiment)。
他给几只大鼠建立了一座袖珍的豪华庄园,整个区域共有16栋相同的“公寓楼”,呈正方形排列,每边各有4栋。每栋建筑包含“4个四单元的复式一室公寓”,总共256个单元,每个单元可以舒适地容纳约15只大鼠。
此外,每栋公寓楼内还有一系列餐厅,楼顶设有饮水喷泉,为其源源不断的提供生存的基本物质,使之成为不愁吃喝的理想国度。
他将4公4母总共8只健康大鼠被放到了这个“大庄园”里。大鼠与人一样,属于“社会性”动物,据说一只成年大鼠的智力相当于8岁儿童。
卡尔霍恩为每只大鼠标注了独特的颜色组合,他或他的团队每天在这个“鼠城”的阁楼中观察数小时,持续了三年多,记录下实验的每一个细节。
这8只老鼠到了大庄园之后,刚开始是探索并且划分地盘。后来这些老鼠开始为了领地、交配权而互相争斗。
老鼠的繁殖能力极强,几乎每两个月翻一倍,在第560天的时候,这个庄园里大鼠数量达到了2200只。然而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事态急转直下,新生幼鼠数量减少,社会行为出现异常。
公老鼠们开始抢夺地盘,撕咬对方,包括想要杀死竞争对手来获得交配权。战败的公老鼠就失去了社会地位,只能跑到一个角落,选择逃避社交,不参与任何活动,选择完全的“躺平”。
它们停止了对于领地与配偶的竞争,有时候互相伤害,但大多数时候被攻击时也不怎么反抗,行为消极,没有社交,时而发怒。
当公老鼠无法再保全领土和家人的时候,部分母鼠取代公鼠。她们减少生育,且比公鼠更加暴力,后来母鼠的攻击行为泛化,开始驱逐并伤害幼崽。
随着暴力升级,一批尚未断奶的幼鼠因失去哺乳而死亡,大量幼鼠陷入到这种充满争斗和焦虑情绪的环境中难以生存。而且上一代的消极回避或者戾气等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下一代幼鼠。
存幸下来的幼鼠失去交配、养育和参与社会的概念,他们将所有时间都用来进食、睡觉、梳理毛发和自我欣赏。卡尔霍恩将这种老鼠称之为“美丽者”(the Beautiful Ones)。
这些“美丽者”无论是公是母,他们都会丧失求偶和繁殖欲望,只有吃饭、睡觉和梳理毛发,完全回避所有社会行为,仅能够表现出与生理生存相兼容的最简单行为。
卡尔霍恩总结道:当所有空间都被挤占,所有社会职位都已填满时,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取胜的代价太大。老鼠的社会关系被打乱,社会行为丧失了意义。同时,很多幼鼠既未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又耳濡目染了竞争的残酷性,早早地丧失了复杂社会行为能力。
整个实验持续1500多天之后,“老鼠乌托邦”宣告失败。尽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但实验结束时,只剩下27只失去生育能力的老鼠。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整个系列实验中,还有一个小实验:
卡尔霍恩给一笼大鼠提供优质水源,为老鼠们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目标”。但是位置设在一个只能容纳两只大鼠并行的过道末端。最初,一只大鼠在水源处仅遇到另一只,两只大鼠都可以通过。
但是不久,越来越多的大鼠都想去饮水,从过道口挤作一团,结果谁也进不去,最后只好放弃,各自回到睡觉的地方休息。这种情况出现多次后,大鼠体重减轻,甚至失水而死。
卡尔霍恩将这种现象称为“行为沉沦”(behavioural sink),即大鼠出于对某地的吸引而形成的“条件化社交接触”。这种吸引力可能导致一种“病态的聚集”,即使这种聚集带来的后果是负面的。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老鼠拥有社会潜意识,个人潜意识,但是没有集体潜意识和表意识,所以拥有集体潜意识和表意识的人类或许会遇到比老鼠还要多的问题。
由于后来科学实验方法的改进,有人质疑这个实验缺乏控制变量和对照组。但是卡尔霍恩的实验进行了多次,并且排除了几乎所有外部因素,比如疾病、天敌、资源匮乏、气候恶劣等等,这项实验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如今的年轻人在内卷社会的下的躺平、自我、回避社交等,是否是一种“行为沉沦”呢?如今考研考公走独木桥的人数下降,甚至出现许多“现在上大学是否还有意义?”的讨论,这是否是一种“行为沉沦”的现象呢?
用卡尔霍恩的话来说:一旦行为沉沦形成,社会行为没有了意义,正常的社会组织和体制,就会崩溃和“消亡”。
但是在当下社会,对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合适的策略?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不跟你们抢,不跟你们争了,反正我也抢不过你们。在家啃老,多添一双碗筷。出门奋斗,掏空六个钱包。
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吃干抹净,又不肯让资源持续流动起来福泽后来者,只让资源在既得利益者手里互相流动,那后来者就没有希望和信心,那他们也不再会继续为既得利益者继续提供养料和社会资源。
长津湖战役到底结束在哪天?
文/ELM
【1】
长津湖战役作为被中共党宣拿出来大肆渲染的朝鲜战争中的战役之一,近几年的讨论热度颇高。不过,讨论慢慢开始有点走形,长津湖战役的存在意义被不断抬高,甚至隐隐有凌驾于二次战役之上的感觉,国内很多公众号在收割爱国主义韭菜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搞清楚长津湖战役和二次战役是什么关系,徒增笑而。
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时间现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党宣手笔,有自媒体揭露,本来结束于1950年12月13日的长津湖战役,在国内的代表性百科网页中,已经被越来越多地篡改为12月24日:
不知道墙内和墙外谁先谁后,更有版面上的前辈版友,言之凿凿地认定:【确切的是24日下午2:36分,最后一艘军舰撤离!】
考虑对韩战多少还是了解一点(比如“第七舰队进驻台海是仅保护台湾还是两边都保护”),本来想写个原创探讨一下,不过搜了一下,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地写了发帖了,于是就转载了这篇《常识流通处|是谁将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日篡改为12月24日?》。
一开始觉得,这不过就是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就事论事即可,哪儿还犯得着上纲上线呢?
没想到,没过几轮,就直接被扣上了个“小心机、小手段”的超大帽子:
【什么刻意不刻意的?每次辩论你总是要搞点小动,不是故意的无限制夸大,就是故意篡改辩论方向!
洪版你是不是缺乏自信?不依赖点小心机,小手段就不敢辩论?能不能大方些,坦荡些!
我们之间辩论,就是玩,不涉及生与死,没必要这样!
二次战役是12月24日结束的。
长津湖战役是二次战役中东线战役!况且,13日之后战斗不断,一直延续!
直到24日美军撤退,轰炸兴南。
算作24日有什么不对?】
我读了之后:
既然这样,礼尚往来,那我就要把之前的原创重新写完,说道说道了,光明正大地摆到台面上,看看到底是谁小心机小手段。
【2】
第一步:审题。
题目问得很清楚:是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时间。是长津湖战役,不是二次战役。后者的范围大多了,包括了西线战役、以长津湖为主体的东线战役,还有其他零零星星的小战斗。
第二步:既然明确了是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时间,那就直接上论据: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英文维基的解释很清楚:On 27 November 1950, the Chinese force surprised the US X Corps commanded by Major General Edward Almond in the Chosin Reservoir area. A brutal 17-day battle in freezing weather soon followed. Between 27 November and 13 December, 30,000[1] United Nations Command troops, later nicknamed "The Chosin Few", under the field command of Major General Oliver P. Smith were encircled and attacked by about 120,000[2] Chinese troops under the command of Song Shilun, who had been ordered by Mao Zedong to destroy the UN forces.
整段就不翻译了,时间点非常清楚:长津湖战役11月27日打响,打了17天,12月13日结束。
然后看中文的。隆重请出当事人、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在1950年12月11日写的“东线战役(也就是长津湖战役)检讨”:
这个证据总归比绝大多数所谓的“军迷”自己拼凑出来的所谓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吧?
什么时候写总结写检讨?当然是战役结束了之后才会有检讨,否则战役都还没结束,那检讨个屁啊?抗战打到43年,进入艰难困苦相持阶段,毛泽东共产党会出来检讨说“不是共军无能,是皇军太厉害”吗?大家心里都清楚啊:战还没打完,还不是最后讨论战果的时候,既谈不上庆功,也谈不上检讨——这才是战役没结束的常规状态啊。
所以,宋时轮在12月11日就发出检讨书,就是知道东线战役(长津湖战役)已经结束,战局已定,给上面的一个交代啊。这个时候不算长津湖战役结束、什么时候算?
如果非要把东线战役(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时间算成24日兴南港联合国军撤退完毕,那就是等于说:宋时轮是在战役的半中拦腰(打了15天,还有13天才结束)的时候发出了自己的检讨书。换句话说:仗还没打完,这个司令就认输了,就检讨了,就怂了,就软了,就已经甘拜下风了。最高指挥官还没打完就认输了,那是不是可以说志愿军其实是输掉了长津湖战役?
倘若非要把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日期算成24日,那其实就是给宋时轮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你这个怂货软包,是不是缺乏自信?是不是只有小心机小手段?本来志愿军战史上记录的是二次战役大胜,你非要中途检讨,你就是在承认二次战役是志愿军失败了是不是?
——如果宋时轮们和中国军史愿意承认自己缺乏自信,只有小心机小手段,入朝二次战役其实是失败、而非胜利,所以需要中途检讨。那我承认一下长津湖战役结束于24日也可以考虑。
【3】
其实,哪怕是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时间不是24日:
【二次战役是12月24日结束的。
长津湖战役是二次战役中东线战役!况且,13日之后战斗不断,一直延续!
直到24日美军撤退,轰炸兴南。】
13日之后战斗不断,——为什么要特别点明13日?因为13日之后的战斗是长津湖战役结束之后、属于二次战役的其他战斗。
那题目问的不是“二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啊,而是“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日期啊,所以为什么要舍弃13日、非要选择24日呢?
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把百团大战的结束日期说成是1945年8月吗?不会啊,因为百团大战结束之后到1945年8月,发生的是“其他不属于百团大战的战斗”。
【4】
至于为什么要篡改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日期为12月24日,转贴和长岛风版友的回答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兹转引如下:
1,有人将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时间篡改为1950年12月24日,无非就是要抵制圣诞节。
12月24日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平安夜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战役结束时间与圣诞节联系,大概是试图制造一种“文化对抗”的象征意义,以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并推动和呼应近年来网络上掀起的“抵制圣诞节”浪潮。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但实际上篡改历史节点不仅无助于真正的历史教育,反而容易模糊真实的历史记忆。
2,他们为什么要故意把长津湖战役结束的日期拼命往后拖呢?不是因为抵制圣诞,而是玩了一个瞒天过海:美军撤离北朝鲜东海岸的最后一个士兵是12月24日,把长津湖战役结束于24日就可以把美国在北朝鲜东海岸所有的兵力都算在长津湖战役上,长津湖与9兵团对阵的就是十万人,第九兵团死伤十万人就显得不那么难看。
不管是抵制圣诞,还是试图玩弄数字游戏,其实都是在掩盖长津湖战役结束于12月13日的事实。
2024年12月29日星期日
说一个司法精神病鉴定冷知识
@李松蔚 PKU:说到司法精神病鉴定,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是冷知识,那就是这种鉴定往往是为当事人家属的利益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当事人减免行为责任。换句话说,没有当事人或家属的授权,医生就没有义务进行诊断或鉴定,也就不存在 “被精神病” 一说。
十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接到过一位街道干部的求助,说一位老人持续造谣污蔑其邻居,已经达到骚扰的程度。接触过的人都感觉老人精神不太正常,可是没办法,老人自己拒绝去医院,子女又很护短,推进不下去。就想让我判断一下老人的病情。
我说我不能判断。不仅是因为我没有诊断的权力,就算有,也不能在这种状况下诊断一个人的精神问题。不管老人表现如何,只要他拒绝就医,就应该把他当做正常人,然后按正常人的办法来。正常被造谣骚扰怎么办?该报警就报警,该起诉就起诉。
街道说,可他确实不正常啊,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你这叫私自赋予了他 “不正常” 的特权,这不行。相当于对方既不用正式成为 “精神病”,同时又享有 “不需要为其行为承担责任” 的特权,这只会让他变本加厉。将来有一天还会缠上你,说你在背后污蔑他是精神病,在侮辱他的人格。你说你是何苦?
街道一下就想明白了。回头再也不说老人有病,就按正常规则办,三下五除二,家属受不了了,说老人家年纪大了确实头脑不清楚,带去看了医生。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一个人做出不正常的行为,就判断是 “精神病”。异常行为可能是因为病,也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坏,或者蠢。“病” 反倒是在帮他们开脱。我被造谣时,也有一种声音说造谣的人是精神病。想得美,都已经在白纸黑字地伪造证据了,哪那么容易就 “精神病” 了?—— 不要主动预设一个人有病,犯错的人首先要被当做正常人,清醒的人,就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承担犯错的代价。
Au Revoir Mon Monde/Goodbye My World/再见我的世界
This animation addresses the timeless question: What would a couple do in the face of the world's end? The answer is both simple and poignant: they choose to stand together and witness the end of the world side by side. Their love may be brief, but it is profoundly powerful.
Performance impression:
Directors: Estelle Bonnardel, Quentin Devred, Baptiste Duchamps, Maxime Foltzer, Florian Maurice, Astrid Novais

普利策奖:戈尔巴乔夫签署苏联解体文件的瞬间
这张照片是刘香成拍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当天拍的。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交接过程,全部是他们指定的美国电视台(都不相信国内自己的电视台)全程纪录,ABC是对戈尔巴乔夫全程记录。最后考虑到要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转播,最后的直播交给了CNN。
刘香成是专门被邀请来的唯一的一名摄影记者。
原计划整个交接仪式在总统办公室进行,考虑到办公室的资料等环境过于复杂。CNN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完全仿造搭建了一个假的总统办公室。办公家具和摆放,都和真的一样。
现场变化很快。戈尔巴乔夫忘记带钢笔了,借了美国记者的笔。刘香成的拍照机会在三十分之一秒中。只要人物动一下,想要的就没了。
当年都是胶卷拍,拍完是不知道有没有的。刘香成拍完后,马上冲出去找了克宫最近的冲印店。看到底片的那一刻,他知道成了。
刘香成拍的这个瞬间就是戈尔巴乔夫正式签署苏联解体的文件后,合上文件夹的虚实一刻。这张照片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
2024年12月28日星期六
陆家嘴没有神话
彼时,证券行业剧烈潮退,用分析师们自己最熟悉的话来描述,就是陷入了 “业绩下滑,估值收缩” 的戴维斯双杀。这个行业曾经承诺的物质回报已如镜花水月,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 ——2021 年还拍着以《闪闪发光的你》为名的券商职场综艺,到了 2023 年都得老老实实学习 “破除金融精英论” 的中纪委文章。
郭博一句 “卖方研究本质上是在为一个时代的资产定价”,颇有中国知识分子 “以天下为己任” 的精神感召。在一切功利主义已变得不大可靠的行业气候下,颇具理想主义的热忱与信念,多多少少对这个人均清北复交的书生圈产生了触动。
文章阅读量超过 10 万,光公众号原文的转发数就超过了 2 万。考虑到国内持证的卖方分析师不过 5000 人左右,文章的影响力显然没有局限于卖方分析师这个小圈子。急需摆脱金融羞耻感的泛金融从业者们,都需要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来抚平向下均值回归的伤痛。
但理想主义的文字在大 A 的走势面前,常常是力有不逮。
2024 年初的 A 股,在公历与农历新年之间的 “垃圾时间” 里,攻其不备地给群众们上演了一场流动性危机,直接把各大指数带崩到近四年的新低,接着 3000 点保卫战就一直打到了国庆节。
在降费、降薪、审计、裁员里大气不敢喘的金融机构们也一直要等到九月底,集体刷屏转发 “金融是国之重器” 的国社社论才稍稍恢复了点精气神。
9 月 26 日晚间,支棱起来的中信证券研究,话不多说就在公众号推文的标题上写了一个 “干”,全然不在乎郭磊那句为时代定价的后半句是,“所以要如履薄冰”。
图片来源:中信证券
围观群众买账,但也不完全买账。
轰轰烈烈的闪电牛只持续了两天,就陷入了箱体震荡的拉锯战。机构们还没来得及完全修复过去三年深埋水下的业绩,行情就陷入了今天炒川大智胜,明天拉莎普爱思,后天做川大归来的诡谲里。
游资和散户谁也不在乎机构重仓的死活 —— 因为蛇年要到了,把葫芦娃拉涨停,因为韩国出事了,把韩建河山拉上去的抽象行为如此似曾相识,以至于不少 00 后都能信手拈来 “远离基本面,收获大阳线” 的顺口溜。
和但斌吵完一架又迅速和解的任泽平,回归主线任务,正式宣布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A 股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而另一位活跃于网络的券商首席陈果在回应 “本轮牛市最大的问题是机构不信” 时,索性把论点升级为了 “散户不信机构” 的问题更突出。
失落的古典定价派和亢奋的赛博网感派,既是 A 股的分裂,也是行业的分野。
这背后是 A 股的主动投资基金经理们,在抵达了鲜花与掌声的巅峰之后,业绩急转直下,信誉持续破产;是在小作文满天飞的 2024 年,丢掉了自己好不容易熬来的定价权。
01
往年的 12 月,是基金经理们争夺年度排名最白热化的阶段。
人们打起 12 分精神,最后再卷一卷业绩排名,好在算年终奖的时候多一点加钱的底气,在猎头找过来的时候抬一点跳槽的要价。但今年机构圈的跨年氛围弥漫着 “没人在意自己是不是第一,都在努力不成为后二分之一” 的活人微死感。
毕竟,做了冠军的人没有迎来规模涨进,而排名垫后的人却要面临被优化的中年。
剔除 ETF 后,公募权益的份额连续 7 个季度持续收缩。即便国庆节后指数一度拉过涨停,基民却在 10 月的牛市氛围里加速净赎回。从资金流向来看,陈果没说错 —— 机构都被群众判去小孩那桌吃饭了,还谈什么相信未来?
基金公司说起来虽是名正言顺的机构投资者,但实际上主动基金经理在 A 股市场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拥有太多话语权的群体。
中金在 2020 年做过一个投资者结构分析,从 2003 年到 2020 年的 17 年时间里,个人投资者始终持有一半以上的 A 股自由流通市值。尤其是 2007 年的大牛市之后,行情持续萎靡,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一路下滑,其中公募基金的份额几乎被蚕食到了边缘地带。到 2014 年的时候,个人投资者占据了 A 股七成多的天下。
图片来源:中国股市生态的四大变化,中金点睛
散户一多,玩法也就荒蛮一些。
不算漫长的 A 股历史,垂名的牛散有一张长长的名单:章盟主、赵老哥、北京炒家、炒股养家,以及公认的前游资天花板 —— 宁波敢死队总舵主徐翔。
在那段只讲涨停板个数,不讲 ROE 增速的时光里,连浓眉大眼的还珠格格,都按耐不住收割的冲动,上演空手套白狼,明晃晃地操纵市场。
随着 2015 年末杭州湾跨海大桥抓捕行动的成功,操纵之风在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之下陷入 “后徐翔时代” 的潮退。主动投资基金经理们,在 2017 年迎来了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如同 1453 年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开启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上半年,游资、牛散被证监会罚没超过 20 亿元,许多券商营业部 500 万元以上的账户被严密监控股票拉抬行为,本来带着杠杆灵活出入的游资被绑住手脚,逐渐分崩。
市场上最为显著的边际增量,就剩下了通过陆港通北上买低估好资产的外资。
公募基金虽然没有旋即出现明显的规模增长,但增量外资是绩优股的主力买家,推动了大白马行情的高歌猛进。坚守价值投资多年的主动基金经理们顺势翻身,基本面的蛋糕日渐做大。
聪明钱知道,所谓的定价权,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掌握在边际增量买家的手里。要追上时代浪潮,就必须在方法论上拥抱变化,在股票池上预判变化。
券商研究所们蜂拥内卷基本面的颗粒度:拆苹果手机那点显学,B 站数码区就能看,直接加码到拆一台比亚迪电车,才能彰显团队对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覆盖。
中国股民也具备非常朴素的实用主义:如果基金是玄学博弈,那我自己就有一套缠论技艺;但如果他们确实有能力形成降维打击,自己既抠不出茅台酒曲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日度经销数据,也养不起团队来覆盖中国庞大产业链的毛细血管,就果断投身到财富搬家的叙事里,团结到 “炒股不如买基金” 的大旗下。
2020 年疫情之后在泛滥的流动性与显著的赚钱效应下,“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 成为了整个基金行业最响亮的一句营销口号。A 股主动基金经理们也顺势迎来了自己名声大噪的高光时刻 —— 白酒造就了一哥,医药造就了一姐,半导体捧出了一代公子,新能源照亮了一众新星。
在明星基金经理之风最为鼎盛的时候,基金行业发布了一份投资者洞察报告,其中最为从业者津津乐道的一条结论就是基民的 “盈利水平与持仓时长正相关”。
就像民政局总觉得来离婚的人不是情感破裂,也不是日子过不下去,都是一时冲动不懂事,需要调解员需要冷静期;基金公司也觉得自己明明是个有潜力的好伴侣,问题主要出在基民不是耐心资本上,那就先给这份爱加一个三年的期限。
从发行数据上看,群众当时确实爱得热烈,虽然知道分手不易,但 2020 年初到 2022 年末,全行业新发的三年持有期基金一共募集了超过 2800 亿的规模。
静态的统计数据经不起 A 股的动态考验
盛世营造出一种 “A 股终于长大、基民终于理性” 的粉红泡泡,连过去只愿意做海外机构长钱的美元 QFII 都在悄悄布局人民币牌照。遑论高瓴、红杉这些一级市场的顶级机构也开始高调宣传自己 A 股的投资能力,衍生出大大小小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平台。
尽管核心资产的估值已经出现明显溢价,基金经理们还在惯性里沿着 “A 股机构化” 的叙事不断线性外推,谁也不会轻易背刺 “长期持有好公司” 的偶像包袱。但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和地缘政治的风险升级已经悄然而至。
外资友军率先撤退,造成的首要冲击就是仅供参考的历史业绩已然不可持续。
“炒股不如买基金” 的叙事在羸弱的基金净值面前不堪一击。万得数据显示,市面上一共有 115 只三年持有期基金(注:统计口径详见下图注释)拥有三年以上的业绩,而过去三年,它们之中只有 2 个能够给持有人带来正回报,整体胜率仅为 1.7%。
发行最火热的表现很惨淡 —— 萧楠管理的易方达高质量严选募集规模 148 亿,三年后,认购资金持有到期时净值不足 0.75,最新净值(2024.12.24)0.74;刘格菘管理的广发行业严选募集规模 148 亿,三年后,认购资金持有到期时净值不足 0.42,最新净值 0.53;赵诣管理的泉果旭源募集规模 99 亿,成立至今只有两年多,最新净值不到 0.77。
主动权益的业绩拉垮,本来还能推卸一句:责任都在美方。可不争气的是,业绩塌房的明星基金经理,职业道德又开始接二连三地爆出污点。
各地证监局从 2023 年开始先后通报了多起涉及公募基金的内幕交易案件,罚没金额总计超过 5000 万元。就像倒车开回了十年前:一边是主动投资的收益率低迷,一边是基金经理的惊天老鼠仓 / 行贿受贿案,哪怕是脱身入私募,也逃不过旧案倒查的如来手掌。
初代基金一哥王亚伟,精准押重组的手法一直笼罩在各种传言之下。今年 2 月,坊间第三次传出王亚伟被带走的消息,其创办的千合资本官方一改过去辟谣口径,公告回应 “因个人原因,王亚伟暂不参与公司运营管理”,反倒给民间留下了更多揣摩空间。
审计署进驻基金公司,小心翼翼的基金经理们在同业饭局上,以前都是问 “涨到哪儿了”,今年都在打听 “查到哪儿了”,给股票定价的时候不一定能做到如履薄冰,但强化岗位意识的时候必然是战战兢兢。机构们也愈发重视税务的合规,喊了那么久的明星基金经理们,这方面也真的赶上了明星的同等待遇。
与此同时,高档写字楼四季如春的办公室外面,无风险收益率已经一路下探到无人区,所有基于过往收益率曲线左侧的投资预期实质上都在面临 “暴雷” 的压力。残酷的凛冬还没完全落下铁幕,主动权益基金们已经欠下了巨大的烂账。
此时此刻尚能喘息,也许只是因为真正的审判尚未开始。
02
人人都盼望一场牛市,但对于基金行业来说,迟来的牛市就是一个残酷的诅咒。
国庆前后的市场躁动里,面对年轻销售们久违的亢奋,基金行业的老人总会想起 2015 年的牛市里公募基金陷入生死存亡的那些日子。
一个少有人关注的事实是,2014 年 9 月初到 2015 年 6 月底,沪深 300 指数上涨超过 80%,是 A 股有史以来最欢乐的三个季度,然而即便是这种 “来不及解释了,抓紧上车” 的行情,主动权益基金始终处在净赎回的压力下。
2015 年三季度,整个主动权益公募基金的份额再度下滑触及历史低点,与 2007 年末形成的总份额高点,构成一个完整的下行周期。
如果说,三季度的净赎回与 7 月初牛熊剧烈转化下发生的流动性危机直接相关,公募基金遭遇挤兑危机,那么二季度大水牛里的份额缩水则是一个反直觉的现象:
2015 年二季度,杠杆牛的狂热冲向顶点,大量主动基金的份额滑向了岌岌可危的份额低点。都说牛市是散户喜欢追高、顺势做规模的好时候,怎么基金经理们反而在最热烈的牛市里,被人民群众抛弃了?
中国第一只开放式公募基金华安创新的份额仅剩下 37.56 亿份,较之前的高峰缩水 74%;景顺长城鼎益的基金份额 13.96 亿份,较高点缩水 88%;博时主题行业基金份额 27.59 亿份,缩水 78%;兴全趋势投资也从 205.36 亿份一路下滑至 47.06 亿份,缩水 77%。
这些基金的份额高点几乎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 ——2007 年大牛市的尾声。
之所以用份额而不是业绩来衡量主动权益基金行业的发展的指标,是因为业绩有时是贝塔,有时是阿尔法,有时啥也不是,但份额始终是人民群众对这个行业的信任投票。
对于 17 年前集中涌入公募基金的投资者而言,启动于 2014 年下半年的牛市,只是让他们在苦等了 7 年之后,才堪堪等到了本金的归来。于是,一场等待时间过于漫长的牛市,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人民群众集中清算 “历史遗留问题” 的窗口。
基金行业素来有一个重要的投资者教育课题,就是如何引导基民不要在回本的时候卖出基金。基金公司的初心也许是好的 —— 回本就卖最有可能卖在牛市前夕,损失未来的收益。
可人类的悲欢在金钱得失上常常是不相通的。
基金行业高高在上,总觉得基金长期(maybe 十年?)来看明明赚钱,基民赚不到钱主要还是非专业人士姿势水平的问题。但机构们却很少老实交代行业自身的缺陷 —— 套住老百姓的时间总是比让大家赚钱的时间更长。
很大程度上,今年 10 月底主动权益基金份额的净赎回速度加快,就是一种历史的重演。只不过 2007 年的牛市之后,08 年的金融危机只用了一年就让基金的业绩腰斩,这轮的高点之后则是三年时间钝刀割肉文火煎心。
2021 年一季度是上一轮牛市的尾声,公募主动权益再次爆发。以易方达基金研究部总经理冯波发行的新基金易方达竞争优势为标志性节点,这只在行业历史上最为畅销的基金之一,限额 150 亿元,最终吸引了 2398.58 亿元的认购,刷新了新发基金认购纪录。然而截至今年 12 月 18 日,这个发行面值 1 元的基金,净值只剩下 0.47。
机构面对业绩压力可以用 “不是只有我们是这样” 作为开脱,但悲哀的正是不止一家基金公司是这样,甚至基金行业不止一次是这样。
公募偏股基金业绩指数 2021 年高点至今整体跌幅超过 30%
基金行业总是在 “好卖不好做” 的时候,把最多的份额卖出去,然后这些 “信任票” 又会在痛苦的过山车里,变成下一轮发展周期开启前要先偿还的 “债务”。
历史早就押好了它的韵脚,却从不简单重复。旧酒以效率更高的方式灌进了新瓶里 —— 互联网的渗透,电商的兴起,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度把曾经长尾的年轻人,一口气全都卷入了 “高位买基金” 的牢笼里。
《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2021 年 10 月)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基金投资年限小于 2 年的新基民占比超过 55%,大量 90 后新基民的涌入,使得 40 岁以下的基民占比达到六成。
也就是说,这一轮基金牛的买账主力,并不是上一轮里已经心灰意冷的老基民终于选择了调解与原谅,而是当时眼神还很清澈的 90 后在 “无知者无畏” 的上头里加速了历史进程。
基金行业的产业链太短,它几乎只生产 “业绩” 这一个产品,评价体系也因此极为单一 —— 基民们终究不会关心基金经理飞得高不高,只会在乎净值做得好不好。耐心可以有,但显然不想以本金腰斩为代价和时间交朋友。失望积攒的年岁太长之后,大牛市归还的本金只会加速人心的彻底流失。
问题只是,下一代眼神清澈没受过伤的婴儿潮在哪里?
基金行业似乎并没有从 2007 年之后那漫长的消亡里真正反思过什么。笔者遇到太多的从业者,总是把主动权益基金的发展滞后归因于 —— 以前有信托刚兑,以前有高息理财,以前有分级 B,以前有 5% 的余额宝,所以老百姓自然看不上波动大夏普低还有道德风险的公募基金。
“以后那些妖魔鬼怪都没有了,如果牛市来了,赚钱效应有了,权益基金就是未来为数不多的蓄水池了。”
专业人士说话的确是严谨,如今总是笼统地说 “权益基金”,而不特地强调主动权益。因为大多数人也都已经看到:新的浪潮已经来临。
03
在造负了两代人之后,基金行业也终于开始翻过 “选基金就是选人” 的这一页。
2024 年,基金份额增长最快的股票基金之一是华泰柏瑞的沪深 300ETF 指数基金。一年不到的时间,它的总份额一路从 374 亿上涨到 969 亿,净资产规模也从 1311 亿飙升到 3975 亿,成为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一只股票型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持有人结构中机构占比超过 80%,第一大持有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家队 —— 中央汇金。
今年年中,中央汇金两个账户(中央汇金投资、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持有这只沪深 300 指数基金的份额高达 363.83 亿份,占比 60%,是 2023 年末持有份额的 5 倍还多。
国家队有救市任务在身,要提振市场的预期和信心,大盘的点位就是其核心 KPI,因此低费率、高流动性的宽基指数自然是其首选。
与此同时,作为熊市里为数不多能持续供应子弹的增量资金,“国家队” 这三个字的带货能力也远胜于任何一个明星基金经理的名字。
连基金公司都不再留恋 “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 的叙事,把口号迭代成了 “买指数就是买国运”。毕竟,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指数基金也更可爱一点 —— 同样都要砸营销费用,指数基金起码不会张腿走掉,明星经理却随时可能提出离职,突然决定回归家庭。
交易大师利弗莫尔曾经说过,趋势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指数基金此番攻城略地,也必然会动摇主动基金经理们的自我定位。
曾在 “一个完整的 A 股市场周期里,平均年化收益率超过 28%,是同期全市场第一” 的兴全明星基金经理谢治宇,最近一次公开发声讲的是《在指数化浪潮中顺势而为》。通过主动投研能力为指数增强基金创造相对比较稳定的超额收益,成为了兴全这个在前二十年里堪称主动权益之光的基金公司面向未来的新战略。
向来摸着美国基金行业过河的中国同行,向外放眼大洋彼岸,被动股票基金规模在 2019 年 8 月超过了主动股票基金。新晋政圈红人 JD 万斯的财富密码全是宽基 ETF,一边大大方方地收着红州乡下人悲歌的版税,一边清清白白地吃着蓝州科技巨头创新的红利。
向内立足本土市场,勤劳的友商们已经把 2024 卷成了指数基金大年,截至三季度末,指数占权益基金的整体比例就已经快进到接近半壁江山。
根据华夏基金发布的《指数基金投资者洞察报告》,今年三季度末,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总规模达 3.5 万亿元,相比 2019 年初激增约 3 万亿元,远超同期公募基金规模的整体增速。
主动明星基金经理们这边厢还没修复自己的业绩和信誉,那边厢已经是一副 “收手吧,外面全是 ETF” 的光景。
在基金经理们风头最盛的 2021 年,很多人对外的标签都是某种维度的中国巴菲特。名校出身的读书人们喜欢说要学巴菲特守正出奇,不越七尺的栏杆,只捡低垂的果实。但事后再看,学习巴菲特本身就是在越七尺栏杆,是拉着基民的积蓄,赌自己是那个万里挑一。
殊不知,自负正在一步步输给估值的泡沫。
实际上,2007 年的时候,巴菲特本人就向华尔街提出一个 50 万美金为赌注的 “十年之约”—— 从 2008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十年间,他打赌低成本的标普 500 指数基金的收益率将超过任何扣除手续费后的对冲基金组合。阿尔法男遍地走的华尔街,只有一个叫做 Ted 的人接受了这个挑战。
十年之后,标普 500 的年化收益率达到 8.33%,Ted 确实输掉了比赛,但巴菲特本人也没有跑赢这个基准。
04
每年一到寒暑假,陆家嘴地铁站的出站口总是能见到带着孩子的游人在四处拍照打卡。这座城市的金融精英们早对这些都市浮华习以为常,行色匆匆地穿梭在租金昂贵的写字楼之间,降噪耳机让他们听不到那些来自小城镇的父母们指着高耸入天的三件套,对孩子灌输的殷切希望:
“你只要好好学习,将来就能到这里上班。”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即便处在一个并不短暂的下行期,基金经理仍然符合中国父母对 “好工作” 的定义 —— 相对仍然高薪,相对仍然体面,无需风餐露宿,无需疲于温饱。
与此同时,对于绝大多数小镇做题家们来说,这也依旧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即便脱离校园步入评价体系多元的社会染缸,成绩好、排名高、解题强仍然是这个行业最有效、最公平的通行券。甚至在很多场合,依然可以凭借自己十几岁时的高考排名、奥赛奖牌而获得更多机会的垂青。
然而,这个一向以绩优主义来刻画人才的行业,不缺乏首屈一指的顶级学府、千挑万选的精英青年,却并没有因为严格选拔、残酷淘汰就真正给老百姓带来长期的获得感。
在绝大多数时候,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基金行业是因为离钱太近而令旁观者羡慕,并不是因为价值创造而让局外人由衷尊敬。
如今,在外部的宏观压力与内部的生存焦虑下,基金公司们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变局里,几乎不去下注昙花一现的天之骄子,也极力避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
很大程度上,此时此刻的基金行业确实需要也依然存在许多勤勤恳恳的普通人,努力为这个行业重拾信任。对于这个本就建立在信任与受托的基础上、牌照的意义是为老百姓谋求福祉的行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The Mad Monk/济公
I think this is one of most underestimated movies by Stephen Chow, who demonstrated his talent in mixing the Buddha's wisdom in jokes and normal life. Every time you watch it, you would be refreshed again. You have more life experience, you would get more impression.
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
券商研究所:时至今日还在卷什么?
文/江东猫草
前两天,卖方分析师行业的年度大奖颁完了。
千禧年伊始,杂志创刊,连续颁了十五年,高潮迭起,成为业内最重要的奖项,和圈外人吃瓜看热闹的排行。2018年骤然中止,此后重启,历经周折,如今已经完全是一个圈内话题了。与“出圈”对应的是“缩圈”,2018年之后,业内三缄其口,谨言慎行,参与评选的研究所逐步减少,对外辐射的影响力也随之变化。
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人,我打个比方:奥斯卡奖颁了很多年,一直是圈内外盛事,直到有一年伍迪艾伦被MeToo谴责品行不端,然后那一届奥斯卡取消了。
不是伍迪艾伦被取消了角逐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资格,也不是他送选的这部片子被cancel,是整界奥斯卡没了,包括评选灯光、舞美、配乐、动画片和改编剧本的人,其他出品方、其他电影……都无了。
后面再重启,奥斯卡还能保持一样的影响力吗?
它仍然没有被替代,但影响力从公域转入业内,卖方分析师的IP价值小了很多,除了极少数总量分析师(主要是宏观、策略),其他行业分析师很难通过撬动奖项的杠杆,获得对公域的影响力。加上2020年之后资产管理规模提升,头部公募机构马太效应明显,影响力减弱的卖方分析师,碰上更有话语权的买方机构,明星公司的定价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也很正常,成熟市场早就这样了。
此时卖方分析师的“名”已经急剧减弱,集中在总量分析师,但“利”还随着佣金规模的增长有过一段时间的提升,直至2023年。
年尾是颁奖季,但比起“荣誉”,而今更引人瞩目的是——时逢监管对行业出台了一系列新管理标准,加强对公开言论的监管,“尤其是首席经济学家、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对外发声的管理工作”。
事情的起因不再赘述了,最后的约束效果肯定会均匀地作用到每个从业者身上;红线的外围是收缩的,形状变化莫测,紧箍咒再念一遍,悟空,不可顽皮。
“名”既缥缈,又有风险,“利”也肉眼可见地缩小了,时至今日,卖方研究所还在卷什么?它还是没有背景的打工人的理想工作吗?
分析师商业模式和研究所定位:成本中心
研究所在券商内部,论营收体量,大多是排不上号的;论利润体量,那就是个弟弟——因为研究所不挣钱。
绝大多数研究所都不挣钱,这个业务模式相当于是机构佣金的两层特许经营:
- 公司层面,以佣金付费制为营收手段,开立席位,提供研究服务,根据研究服务的价值分配交易席位,挣取交易佣金。收入是佣金,成本是席位费、人力成本、数据库、支付专家费用、办会,以及支付各种展业成本,其中养分析师是最大的人力成本。
- 分析师层面,团队和公司有一个分佣契约(每家公司不一样,一般提供佣金收入的2-5成作为前台业务人员的毛收入),相当于以一定比例的租借使用费,拿了公司给的特许经营执照,同时把中后台支持性工作交给公司,在合规范畴内提供比较独立的研究服务。收入是佣金的一部分,成本是团队全部成员薪资、差旅和展业费用;有些公司会把数据服务、工位费之类算到franchise费用里,有些会全部给到分析师团队承担。
尽管大多数公司不会有明确的表给你核对,但考核方式是非常清晰和透明的。结果导向,外部评价,明码标价,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实在是奋斗逼首选的那一档工作。
券商研究所这个业务模式,是最容易弯道超车的:没有Capex,研究对象是上市公司,而客户信息都在水上,能见度都很高,人是最大的开支。你只要敢给激励,招分析师,小公司也很容易快速树立研究所的品牌,然后以此为流量入口,拓展其他业务。
在巅峰时候,这行业天然有互联网思维:羊毛出在狗身上,猪买单。研究所被认为是一个成本中心,不要求盈利,很多小券商甚至愿意长期由集团拨款,以超过营收规模的投入去支持研究所的业务发展。
这就是一个好工作的前提条件:在员工、客户、股东利益的不可能三角里,战略性放弃股东利益,把价值分配给员工。
(能打破这个三角的,往往都有点禀赋资源,或者羊毛出在狗身上的办法)
留给集团股东的很少,分给员工的很多,给个人定价,有IP价值,一般符合这个条件的行业都是打工仔的天堂:MCN、律师事务所、影视剧、券商分析师……
至少是腰部以上打工仔的天堂。
事至如今,流量入口、成本中心的前提发生了动摇:没有什么“其他业务”了,股东还能战略性放弃利益吗?
做大入口是为了迎来送往做生意,现在生意变少了。好比你投流获客,获来的用户逐渐边缘化,终身价值还不如买量的成本贵,这个客还有什么意义?
影响力与合规的两难
本次监管又再次明确了会议纪要、调研纪要不可以任何形式外发。我还在岗的时候,每次看到友商的有道云纪要,都要憨憨震惊一下:怎么还敢写,还敢发,这是不要命了吗?
不可以,不允许,后患无穷。云纪要的传播根本没法控制,回头就给你挂到纪要网站和收费社群里了,你想对客户贴心一点,其结果就是盗版网站挣走了流量,所有的锅都是分析师背着。他在暗、你在明,谁来背着这口锅,还不清楚吗?
实操里,因为过度竞争、服务同质化,分析师很难拒绝客户“发纪要”的要求,你不发、别人发,国内不是研究付费制,更不是计件工资,所有的乙方都要提供情绪价值,“服从”是情绪价值里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你特立独行也行,除非你有非常不可替代的价值,否则特立独行一定会影响你的天花板——你都是个行商了,连当坐商的资格都没有,还要吊起来卖吗?
严格执行监管要求,卖方研究的价值就会不断下降,原因很简单:监管要求是透明、公平、同步,而谁会为公开发的报告付钱?让我们再复习一下生态环境:竞争是过度的,供给是同质的,收费标准是降低的,市占率是必须抢的。
↑以上这句话适用于大多数行业的现状。
不同于外资卖方,大多数报告不是公开的,索取报告本身也收费;国内几乎所有卖方团队都有公众号,会发出报告的重要观点、乃至报告全文。对影响力的追求使得大家期期艾艾地在合规边缘找空白地带——分析师是to大B的,他们服务的是合规投资人中的佣金客户。
但你想展业吗?那你就要服务暂时没有给你付佣金的潜在客户;
你想拿奖吗?那你就要服务永远不会给你付佣金的投资人。
你想出名吗?那你就不要介意把报告登出来给所有人看。
怎么办?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是你的佣金客户,你只能在公众号里期期艾艾地写免责声明:如果你不是机构投资者而不小心看到了,请自戳双目,我们对一切结果不负责。
人都有KPI的,没有,就制造一个,送给老板当做管理抓手。年末的述职报告里,你还得写:我们平均每篇报告的阅读量达到……。
其实哪有那么多客户对你那几个【】公司感兴趣,而且客户可以听你路演,有几个人真看公众号报告。
实际上如果细扣监管要求,会发现一切动作都可以不合规。报告基于公开资料和不涉及内幕的调研信息,而你和客户沟通的内容不能超过报告,否则就涉嫌提供信息差,对投资人没有一视同仁;你不可以在发报告之前和重要客户沟通,领会精神,杜绝风险的话,所有的沟通都应该是公开报告内容,在非交易时段同步给所有投资人。
你除了朗诵已经发布的报告之外,所有动作,严格来说都是有合规隐患的,毕竟细究一下条例、理解背后的出发点,很简单:公平、透明、一视同仁。2018年之后还拼命做影响力的行为经常是左右互博,券商最重要的东西是评级,研究所活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漏风口多得跟蜂窝煤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研究所本身才能挣几个钱?扣分了怎么办。
而且在实操上它会更麻烦:由于条例极其严格,几乎没有展业可能,水下的模糊操作就变得很普遍;水下动作一普遍,加上从严监管和需要较强自我管理意识的舆论地位,能炸的风险点就增加了,比如A客户把B公司的专家纪要拿给了公司看,公司把专家辞退了,然后反手把你告了,还公开骂分析师请了假专家……
这样的客户真的不少,也不知道什么迷の心态,好想把汉堡王那一行“我们不告密”做成贴纸,贴他们办公桌上。
遇到这种事,除了就地跪好,磕头认错,猛抽自己两大耳光,没有别的办法。
更不要说有些事情和是非无关,主要和影响有关,分析师总想获得影响力,增加谈判筹码和潜在出路,但是影响力是怀璧其罪的东西。大量知识付费、私域社区和信息汇总自媒体的存在,放大了分析师的风险:还是那句话,他们在暗,你在明;流量是别人的,出了事这口锅只能给你。
非常讽刺的是,分析师看似非常体面,高学历、高收入、自由流动,好像非常有自尊,其实在券商内部,研究所是个地位不高的部门。不挣钱只在其次,关键是离客户近、离总部远,分析师都是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清高,斗争经验非常匮乏,加上年景好的时候总跳槽,根基不深,在总部根本说不上话。
这影响力你还要不要,怎么要?怎么在合规的范畴内要?怎么这么多既要、又要、且要、还要。
卷,是生存的必须,还是路径依赖?
24年7月1日新规启动,同等交易量下,卖方的佣金收入砍去4成。
如果不是9月底一波快牛把交易量拉起来了,今年的卖方收入是进了ICU的。
但你要问牛市对体感的影响,我觉得改善不大;给我讲述今年卷度的卖方,说得伤感的话是——今年大大小小办了11场会,比大姨妈还勤,行情是这样,也不知道在卷啥。
众所周知这个行业过于高压,生理周期正常的人不是很多。11场会,那肯定是勤过了大多数人的大姨妈,可能也勤过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毕竟咱东亚职场人,谁还能不懂——我举个日本的婚后无【】数据,见微知著:
(这个图不翻译了,播客里聊)
收入是下降的,越升机会是减少的,办会成本是提升的,服务频次是急剧增长的。买方也很累,不想接受那么多服务,卖方也累,派点不值钱啊,时薪急速下降,总工作量卷出新高,每个人都更难受了,为什么?
很多人误以为生态环境改变,物种会躺平来自适应,这就太不理解竞争了。
不会的。一定会在增量转存量、甚至是缩量竞争的初期卷出新高——不知道什么是“保障”、一切满足都依赖增长,一定会在总量收缩的时候发生激烈的生存竞争。
对公司来说很简单,费率下降意味着要头部集中,要留在牌桌上,不想被淘汰。
对个人来说也一样,拦腰砍你一刀,砍掉一半收入,要求你提升工作量,把时薪降低到过去的1/3,你又能怎样?你能不还贷款吗?现在还能跳到互联网、跳到实业吗?
派点比服务滞后一个季度,佣金滞后两个季度;每个人都不见棺材不掉泪,计划必须前置,投入必须增大,路径依赖是一定的,就算知道会入不敷出,也务求要不计成本地留在牌桌上——生存竞争的经验刻在我们每个人基因里:不能留在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了。
你要不留在桌上,明年供给侧又改革了。
农业文明是有一些基因在骨子里的,躺不平,气候变化莫测,总要为饥寒做储备。
望江楼上有一副长联,没有大观楼上那一副知名,但现在的我更喜欢这个;上联的结尾慷慨激昂,“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下联气势转弱,消沉痛楚,“且向危楼俯首,看看看,哪一片云,是我的天。”
气势没能更上一层楼,泄了,所以诗不好。可是这样的对联,是有些谶语气息在里面的——曾经是有气势的,有梦想的,诗人吊古,猛士筹边,鸿篇巨制,装演英雄;可是最后呢?嗟余蹙蹙,四海无归。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对这副对联嗤之以鼻,觉得颓败成这样,控制不住的拉垮,真是格调不行;现在宽容了很多,人到中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跳进水里的人看着船上的人,站在船舷的又凝视水里的,都道不如归。
坚持下去,留在桌上,生命会找到出路。
李稻葵:中央政府将发行大量债券,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并支付拖欠款项
原标题为《前央行顾问李稻葵:中央政府将发行大量债券,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并支付拖欠款项,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恢复消费者信心》。
主持人:
对于财政部周末发表的言论,您的初步评估如何?
李稻葵:
我认为在政策调整方向上,财政部长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政府需要迅速且大规模地增加债券发行,以支持地方政府。这个方向非常准确。然而,他并未明确说明新的中央政府债务发行的具体数额。为此,他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的支持。好在中国的全国人大没有两党之争。一旦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全国人大就会迅速跟进。因此,我预计到本月底,中央政府债务将会大幅增加。中央政府将利用这些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获得现金后,将支付拖欠给员工和承包商的款项。随后,实体经济将重回正轨。
主持人:
您提到可能还有进一步刺激的空间。我想知道,您是否认为他们可能会重复去年的做法,将财政赤字目标提高到3%以上?或者您认为现在这样做是否为时已晚?这样做现在还重要吗?
李稻葵:
今年5%的GDP增长率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从技术上讲,这个目标将会实现。5.0是实际GDP增长,而实际GDP增长实际上是名义GDP增长除以GDP平减指数。平减指数是个谜——没人真正知道它的具体数值。所以5.0从技术上讲不是一个大问题,最终它会实现。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经济在明年和后年继续增长。经济如何从当前的困境中恢复?当前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地方政府正在耗尽现金。地方政府一直在使用短期债务和贷款来为20-30年的长期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要求地方政府在未来一两年内偿还债务是不合理的,甚至是疯狂或严酷的。这是一个自我造成的伤害。
最终,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需要发行大量债券来置换地方政府债务。这不仅仅是赤字管理,而是资本账户管理。中央政府有资产和负债,他们必须管理这个资本账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央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中央政府,持有最赚钱的商业银行和三大最赚钱的移动电话运营商的股份。中央政府没有理由不发行大量债务来帮助地方政府,进而帮助宏观经济。
主持人:
从专业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认为许多外国投资者过于关注一个可能意味着中央政府预算赤字增加的大数字。还有扩大预算赤字的问题,其中包括专项债券、地方政府,当然还有你提到的这种转移。那么,请告诉我们你认为整体预算赤字应该是多少。考虑到所有因素——中央银行、中央政府预算赤字、地方政府支出——明年和后年的财政缺口应该有多大,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这种通缩螺旋?
李稻葵:
简单回答一下,我认为3%的赤字,最多5%,就已经足够了。但我的关键点是,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正在用传统的方式思考中央政府的当前收入和当前支出,并将差额称为赤字或盈余。中央政府需要做的是管理资产和负债账户。中国中央政府在股票市场上持有大量资产,比如六家最赚钱的商业银行等上市公司。同时,中央政府持有的债务很少,最多只占GDP的25%。所以中央政府有巨大的净资产。
中央政府应该做的是发行更多负债,发行更多债务,并用这些钱来购买或置换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项目形式存在的资产。这是资本账户管理。用公司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并购操作。这不是支出或资本开支,不是关于经常账户的,而是关于资产管理的。所以我真的相信我们经济学家必须研究公共财政。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个新的框架来向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和普通大众解释这一点。
主持人:
大卫,我想谈谈你在上一段中提到的关于政策走向的问题。看起来政策方向终于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了,这可能比我们得到的具体规模更重要。你认为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这种转变?你认为是什么促使了这种转变?
李稻葵:
从根本上说,这是宏观经济的现实。非常简单。每个人都知道地方政府是最大的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坦白说,它们通常支出占GDP的41%,包括常规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提醒你,家庭消费支出只占GDP的38%。所以当地方政府的支出从占GDP的41%缩减到今天的36%——减少了5%——难怪经济会萎缩和收缩。
最终,政策制定者明白了这一点。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在推动地方政府偿还短期债务,勒紧裤腰带。这么做是疯狂的,自杀式的。这是自己造成的伤害。我在中国已经反对之前的政策2-3年了。最终,正如我们在中国所说,现实比任何学者的论点都更有力。现实正在显现,我们的高层决策者正在接受这一点。
解决方案非常简单,因为中央政府在资产方面确实很富有。我说的是它的净资产状况。它非常高,持有大量盈利股份。他们可以发行债务。所以这是正确的方向,我认为这解决了是否有钱可以花的问题。
主持人: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资金应该如何最好地使用以达到5%的增长目标。你在项目上投资,就能达到5%。现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措施、可用的资金以及他们表示将要投资的领域,能否解决消费者信心危机?
李稻葵:
是的。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地方政府已经推迟或延期了大量支付。他们推迟支付给承包商、员工——直接或间接的——有多少钱?占GDP的10%。我自己也对这个巨大的数额感到惊讶。我现在说的是占GDP 10%的延迟支付给各种公司和员工的款项。难怪消费者不愿意花钱——他们根本没有收到钱!
所以这是支出的首要来源。相对而言,不要让地方政府做太多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要支付给为你工作的每个人,包括那些在疫情期间为他们辛勤工作的人。付钱给他们。给他们现金。这不仅是履行合同,尊重良好合同精神——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短期经济刺激。换句话说,最大的经济刺激就是让地方政府偿还拖欠公司和员工的款项。就是这样。这一件事——占GDP的10%就在那里。非常简单。